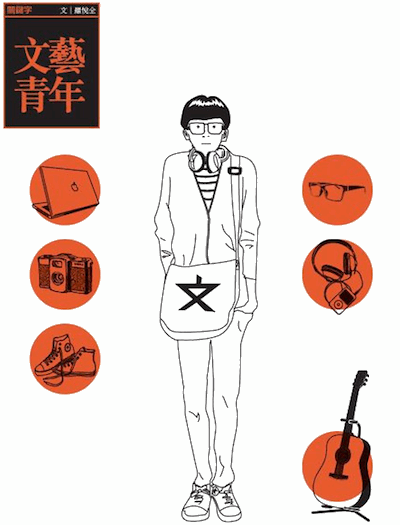* 本文發表於《藝術家》雜誌,2017年8月號 | 羅悅全
「故而本土或在地的觀念,是和自我肯定不可分的[…],這個本土/在地不會是一個異己的圖騰,因為本土/在地不是一個外在於『我們』的東西。或者,用比較文學一點的說法:『本土』是一個只要你抵抗,就立足其上的地方,不是一個遙遠的聖地。」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顛ㄈㄨ\中心」的戰鬥與遊戲》[1],1991
1995年的後工業藝術祭(又名第二屆破爛生活節)結束後不久的一個炎熱中午,我路經師大附近巷弄,看到牆上貼著海報,寫著「第三屆破爛生活節──有音樂和表演」。我興沖沖地趕到海報所指的地址,是一片夾在老式住房之間長滿雜草的荒地,約莫四十坪,七八位年輕男女閒聊著,角落一棵矮樹下掛著蚊帳,還有一堆雜物,似乎有個流浪漢佔領了此地在那裡過日子。空地中間是台廢棄的鋼琴,機件都鏽了,似乎得用腳踩在鍵盤上才能勉強發出聲音,我等得無聊,真的這麼作了。表演一直沒開始,我詢問那群男女,他們指著蚊帳笑著回答:「等XX回來就開始了。」過了半晌,一位貌似研究生的男子匆匆到場,把肩上的書包扔到一邊,按下旁邊手提卡帶機的按鍵放起音樂,對著其他人喊著:「來來,大家站起來,跟我一起動!跟我一起唱!」為數不多的觀眾聚攏上來隨著那男子的吆喝開始揮動雙臂、抬腿、扭腰、……「來來來,這場表演裡,我們大家都是表演者!」帶頭的男子喊著,像是回答我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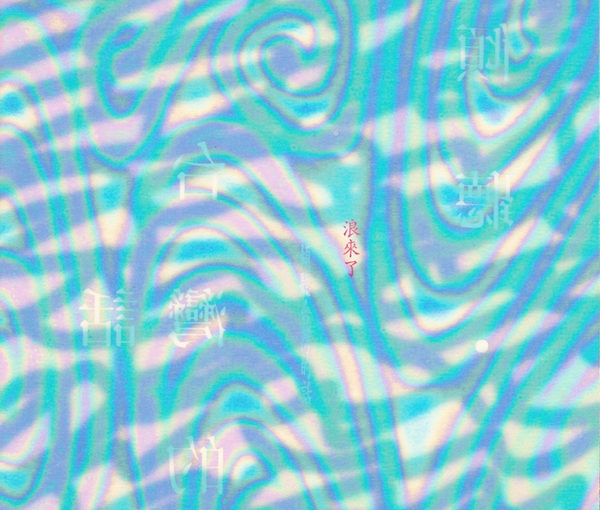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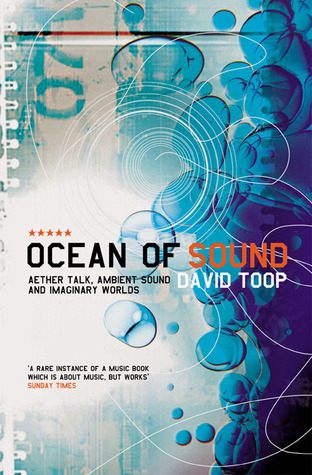 10/17日,David Toop 將於北藝作一場講座與演出,隔日Yannick Dauby 於失聲祭演出,10/19日,兩人則將在立方計劃空間對談。
10/17日,David Toop 將於北藝作一場講座與演出,隔日Yannick Dauby 於失聲祭演出,10/19日,兩人則將在立方計劃空間對談。 從來沒想過有機會在凌威開的店裡DJ,各位有空歡迎來聽我放音樂。
從來沒想過有機會在凌威開的店裡DJ,各位有空歡迎來聽我放音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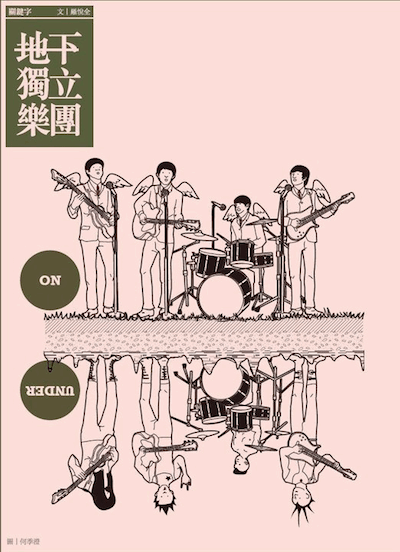 (原文登載於
(原文登載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