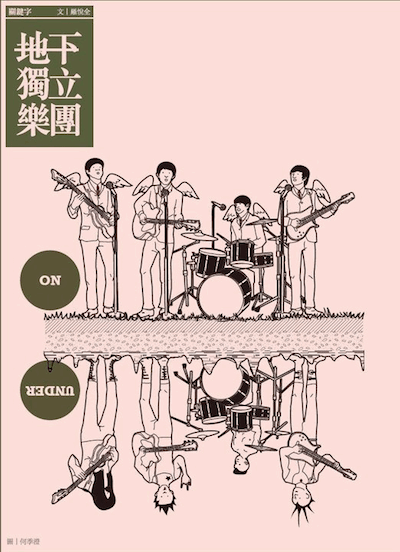 (原文登載於《今藝術》2010年十一月號,Artickle別冊)
(原文登載於《今藝術》2010年十一月號,Artickle別冊)
文/羅悅全; 圖/何季澄(《今藝術》提供)
在《海角七號》創下國片賣座紀錄後,台灣接連出現兩部以樂團為主題的電影:《一席之地》、《混混天團》。電視偶像劇也相當熱鬧:《終極一家》、《紫玫瑰》、《死了都要愛》同樣以樂團為主題,「搞樂團」似乎是情愛之外,編劇作家對台灣年輕人理想主義最浪漫的想像。實際生活中,每年都有海洋音樂祭、春天吶喊等萬人參與的大型戶外表演。在台北,除了The Wall 、河岸留言、Legacy、…等等有樂團表演的live house。每到週末,走到西門町、台北當代藝術館門口、天母商圈、龍山寺地下道,路上就有機會看到樂團表演。樂團的音樂風格各有不同,一致之處是他們大都採取傳統搖滾四件式(套鼓、貝斯、吉他、主唱)或五件式(加上鍵盤)的編制,團員各司其職,更重要的,是這些樂團唱的都是自已寫的歌。「搞團得唱創作歌曲」如今已如吃飯就得配菜一般天生自然,我們幾乎都忘記了如此簡單的條件是走過什麼樣的路演變來的。
我們或許還記得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西洋民謠演唱會」喊出「唱自己的歌」與之後的民歌運動,但不提我們都忘了,「樂團」在 80年代的台灣還不叫作「樂團」,而是名為「合唱團」,例如「丘丘合唱團」、「幻眼合唱團」。那時候的流行音樂,只有拿麥克風才算數,演奏樂器不被當一回事。
不提我們都忘了,台灣搖滾樂團先驅之一的「紅螞蟻合唱團」80年代初於台視的「大學城全國大專創作歌謠比賽」一路過關斬將,最後卻因為被眼尖的評審發現鼓手「沒開口唱」而遭淘汰。
不提我們都忘了,即便到了90年代初,台灣樂團在現場要唱創作歌曲得冒著被噓的風險。因為容許樂團的場合僅限於少數幾家「西餐廳」,觀眾進入搖滾樂團駐唱的餐廳裡,期待台上是老鷹、山塔那、槍與玫瑰、…等等美國樂團的分身,期待樂團在喝酒用餐時提供虛擬的美國氛圍,觀眾潛意識裡拒絕樂團用自創歌曲把他們帶回台灣現實。
台灣現實是,戒嚴意識壓抑了「唱自己的歌」口號中隱含的台灣本土意識、反抗意識,藉著民歌運動出線的歌手、詞曲作者雖然建立了新的流行音樂體系,但不滿現狀的年輕人仍無法在當時的流行歌曲找到渲洩的出口,只能繼續從西洋搖滾樂團裡探尋。
直到80年代末解嚴後,「本土」與「反抗」才重新被提起。1987年成立的水晶唱片是一串事情的開始,他們發行了《搖滾客》雜誌,引介了幾個新鮮名詞和概念:「地下」、「獨立」、「另類」、「非主流」。這幾個後來常放在「樂團」二字前面的詞,都包含了對台灣流行音樂與環境的不滿與對抗的成份。其中「地下樂團」這個詞的出現頻率,比其他排列組合都要來得高,用來指涉開始試圖在現場中演唱創作歌曲的搖滾樂團。例如於1988年發表首張專輯,被稱為「台灣第一組地下樂團」的Double X;「友善的狗」唱片於1994年有計劃地發行了一系列台灣重金屬、龐客樂團的首張專輯,包括刺客、骨肉皮、濁水溪公社、…等,這個系列叫作《台灣地下音樂檔案》。
但是搞團的樂手並不喜歡被稱作「地下樂團」。「地下」在西方是具有反文化意義的字,拿到剛解嚴沒多久的台灣卻脫脈絡地被簡單理解為沒名氣、粗糙、業餘,甚至聯想到非法。此外,台灣社會對樂團也充滿敵意,除了媒體時常誇大戶外音樂祭現場發生雜交、販毒、嗑藥的新聞,樂團固定的表演場地-live house -因為在法令上妾身未明,屢屢遭到政府刁難。90年代期最早出現的live house-Scum,就因為多張巨額罰單,搬了三次家,最後於96年不堪虧損結束營業。進入2000年代,情況也未有改善。
差不多在這時候,關鍵字從「地下樂團」轉移到「獨立樂團」:只要是未與大唱片公司簽約,有較高自主性的樂團,就是「獨立樂團」。這種解釋對急於爭取認同與合法地位的音樂事業經者來說,相對方便許多,而且它的確有效。
2005年,地下社會、The Wall等台北著名live house因為營業登記項目不符的問題而被警方連續開單處罰,面臨無法生存的困境。立委林濁水2006年於《蘋果日報》的專欄為爭取獨立樂團的表演場所說項,文中將獨立樂團、live house涵括進「文化創意產業」,隨後林濁水又與立委林淑芬召開公聽會要求政府改善,文建會隨後同意發予各家live house「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明書」作為護身符,未來再透過修法來解決營業項目登記的問題。
在此關鍵事件後,「獨立樂團」終於取得官方的認可,這也意味著整個台灣社會對樂團的敵意已經緩和,並且轉向正面。
新聞局於2007年起開辦「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案,遴選優秀樂團補助專輯製作經費;2009年開始補助樂團出國參加國際音樂活動;2010舉辦專為獨立樂團而設的「金音創作獎」。今年五都選舉,新北市市長候選人蔡英文宣佈將「提供獨立樂團更多表演空間」列為政見。2010年貢寮「海洋音樂祭」的競賽項目「海洋獨立音樂大賞」,報名件數達213件…。獨立樂團的唱片銷售數字雖然沒有顯著成長,有趣的是,由於主流唱片銷售量年年走下坡,對比之下,幾組一線獨立樂團的銷售成績居然不算太差。種種跡相看來,獨立樂團的情勢一片大好。
等等…,事情好像有點不對勁,若從字面上來看,接受了政府補助的「獨立樂團」還能稱作「獨立」麼?不提我們又要忘了,曾經,只要是搞樂團,風格是搖滾樂,唱的是創作歌曲,站上台刷下電吉他就具備了叛逆的態度。現在要叛逆,好像不那麼容易了?沒有人會想回到過去,只是回想起過去,不禁令人產生一點莫名的失落。
我記得伍佰曾經談到地下樂團,他說他比較喜歡創作樂團的說法,這點我有同意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談創作,避免的地下或獨立等主觀認定,而是回到音樂為出發點,我們是創作樂團,我們自己寫歌…等
但是創作本身也是有些弔詭,資訊流通的結果也造成相互影響的頻繁,我們可以見到某某樂團唱自己的歌並不是從李雙澤式的文化省思,而是鍾愛某某樂團/某某型態的曲風而來的複製貼上遊戲,當然這不是抄襲,講誰抄襲都過於嚴苛。同時李雙澤不也是受到西洋民歌啟發嗎!
當然,這樣的鍾愛也不是非得要叛逆與落魄,幾部台灣電影談到的樂團過程都過於強調這樣的顯而易見的情調,這不是不行,套用竇唯的說法:搖滾樂也只是音樂汪洋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貌,要選擇叛逆,當個飆車族不是更為直接嗎(當然這不是鼓勵飆車,只是一種譬喻)。
其實重點是「反抗意識」,也就是知道自己在作什麼,為何而作,目的為何的。
和你說的那種不清楚目的的「叛逆」是不一樣的事情。
的確,重點是反抗意識,但這是不是表示知道自己在作什麼為何而作目的為何,我持保留看法。
至於叛逆,也可以是很直觀的,甚至是沒有經過理性思考的,或是所謂由身體感官來思考的,但這不是就表示不清楚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我也持保留看法。
當然,問題也可以是,為什麼要知道自己在作什麼/為何而作/目的為何!(即便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的想法是,從10年前阿帕的玩團最屌,玩團就已經走出叛逆與社會意識的包袱,而是回歸到一種休閒娛樂的類別;喜歡,所以去,這是最基本的出發點不是嗎?
不受歡迎/不被認同/有志難伸/反抗品味/這些種種隨著時代變遷,或增或減;但也不限於搖滾樂或說音樂;因為愛一個人而愛一首歌,因為熟悉所以陌生,因為懂了所以不發一語。
玩團的人有很多種。並不是每一種都是我關心的。
哈,我還想到另一個現在聽來蠻尷尬的詞:「熱門音樂」。
印象中1990年代仍有不少大學院校(還是只有中南部?)裡的搖滾樂,還是登記為「熱門音樂社」或「熱音社」。在「獨立搖滾」成為風潮之前,這名稱似乎像是一個讓學校官方較能理解的「搞搖滾」代稱,即「非民謠非古典,演奏的全是插電樂器」云云。所以社團公演時仍不乏出現「熱門音樂表演」的說法,現在聽來應該足已讓熱血的滾青們羞憤自殺吧。近乎把搖滾樂閹割掉似的。
如果1990年代後的「獨立搖滾」主要透過跨校連盟產生,「熱門音樂」感覺比較像是在校內管制下存在的類型。整個產生的語境還蠻相對的。想想究竟台灣1990年代以來的搖滾樂,是如何透過社團模式在大專院校內被官方接受?似乎是個蠻有趣的事情。
總之,還蠻好奇「熱門音樂」這說法的脈絡(似乎它的流行跟1980年代的余光音樂雜誌有很大關係?)
找時間寫寫這個關鍵字如何? 就當觀眾點播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