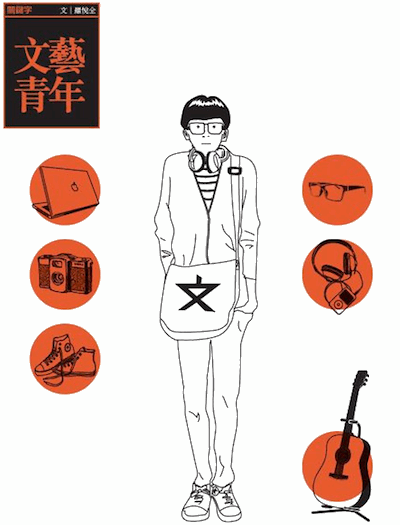
(本文精簡版登載於《今藝術》2010年九月號,Artickle別冊,插圖由《今藝術》提供)
大約在2008年,網路流傳一篇〈文青一百問〉評量表,其實未足一百題,出處不可考,有多種版本,基本上是集體創作,網民帶著挖苦的意味拼湊出「文藝青年」的面貌。略舉部份內容:
文青都愛村上春樹、文青喜歡歐洲遠勝過美洲、文青不用無名小站、 文青愛去誠品看書、文青都在很暗的咖啡館看書、文青煙抽很大、文青咖啡喝很大、文青酒喝很大、文青一定要有Mac筆電、文青要會樂器、…
許多部落客將其當成心理測驗,計算命中幾項,得到似失望似慶幸的結論:「還好我不是文藝青年」。
「不知道多久以前開始,『文藝青年』開始變成一個黏膩撕不掉的標籤令人不快,不是不想承認但也不願被貼上,畢竟骨子裡的基因比起遙遠時代的文藝青年已經演化好幾番了。」
上面是2007年由誠品書店主辦的「我不是文藝青年2」系列講座的文案,它召喚的是文藝青年。新世代文藝青年自嘲為「假文青」、「偽文青」,表示他們心中還有一種「真文青」,但那是上一代的東西。至於「真文藝青年」是什麼模樣,少有人提。
尋找「真文藝青年」的樣貌,應該從塵封的歷史檔案中翻找,抽樣看看「文藝青年」如何一代代演進。我們不妨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找尋。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出現40多個文藝社團。合理推判,「文藝青年」一詞應是從大量文學刊物與筆戰中誕生。
手上能找到的資料,最早出現「文藝青年」四個字的是左派文人郭沫若於1928年以筆名「麥克昂」在《文化批判》中發表的〈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態度的考察〉,文中批評文藝青年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要求:
「文藝青年們應該做一個留聲機器—-就是說,應該克服自己舊有的個人主義,而來參加集體的社會運動。」
另一份早年關於「文藝青年」的文獻是1933年江蘇鹽城縣出版的週報《文藝青年》,刊登翻譯小說與愛因斯坦、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柯勒惠支等人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宣言等文章。這份週報的創辦人當時21歲,名叫胡喬木,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左右手。1940年,香港也發行了一份《文藝青年》的半月刊,同樣由左翼文青創辦,關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抗戰期間香港的暢銷刊物。
活在21世紀的我們可以想像但很難體會當時的文藝青年在左派文人屢屢召喚拉攏下到底轉化出什麼神奇的力量而如此受共產黨寵愛?
無論如何,國民黨肯定吃了不少文藝青年的虧,徹退到台灣沒多久,在蔣介石直接命令下,於1951年10月31日「蔣公誕辰紀念日」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掌管青年政治思想,由蔣經國擔任首任主任。救國團附屬單位「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其宗旨的一條是:
「本會所負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文藝青年,成為一支堅強的筆隊伍,共同為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任務而奮鬥。」
該協會1954年出版刊物《幼獅文藝》(刊名從英譯「Youth Literary」而得-也就是「青年文藝」);1955年「戰鬥文藝營」開辦;除此之外,各縣市還有對所有中學生免費發送,形同強迫訂閱的文藝雜誌《X市(縣)青年》。「文藝青年」正式被國家列管。
這段文學戒嚴的時代,若不是走官方扶持的「反共文藝」、「戰鬥文藝」,便必需標榜與政治無涉的「純文藝」。若作家不小心顯露異於官方的寫作路線,小則幾場筆戰,大則查禁停刊甚至入獄。在這種不能碰政治甚至不能碰現實的環境下,企圖走「純文藝」的文藝青年,其處境必定虛無不踏實,如1983年林懷民於聯合報談到張照堂:
「六十年代,許多人在『存在』,在『虛無』,包括我自已。有趣而可喜的是六十年代敏感的文藝青年安然渡過七十年代,許多成為腳踏實地的文藝工作者。」
到了解嚴後的90年代,走出牢籠的文藝青年,虛無與苦悶並未煙消雲散,這個世代的文藝青年有另一種奇怪的、與過去不同的苦悶。馬世芳於1990年在《台大人文報》所發表的〈我如何成為一箇文藝青年〉生動地描述了解嚴後文藝青年的心境,甚至可說是精準定義了解嚴後至今的「文藝青年」形象:
「不幸的是無論如何都鬱悶不起來。……所謂『鬱悶不起來』和『不鬱悶』是不一樣的。……吸菸。聽極其沉淪殘酷的搖滾樂。弄亂頭髮。喫難喫的午餐。坐在活大餐廳喝冰咖啡唸攝影蒙太奇的原文書。還是鬱悶不起來。……我的夢想是,在一個四到五人的搖滾樂團裡當主奏吉他手,……。留長長長長的頭髮和滿嘴滿臉的髭鬚,也許叨一支Salem涼菸,也許,呃,唱得渴了就喝口啤酒。歌當然是唱自己寫的。……除了藍調,還可以吼叫一些龐克,刷著嘎啞刺耳的電吉他:我是個反基督!/我是個無政府!/不知道要什麼可是知道怎樣要,/我要打爛經過的傢伙!/因為──我要做──無政府!…」
解嚴後,以前不能談、不能讀的出版品大量湧進,《資本論》繁體中文版上市、新馬理論書籍汗牛充棟,文學之外,西方電影、搖滾樂中反文化的成份也得以重新解讀。但是,解嚴後台灣知識分子的聲音已被眾聲喧嘩淹沒。救國團四十多年來建立的文藝系統,其光環隨著解嚴崩毀,新的文藝生態未及建立,新媒體卻透過報禁開放、電台解禁快速全面包圍台灣人的閱聽。1995年,純文學出版社結束營業,正好標示「純文學」在台灣的命運。同年,有支叫作「文藝青年」的樂團改名為「無聊男子團結組織」,無意中也正好標示文藝青年形象的改變。文藝失去讀者、失去市場,也失去力量,能存活下來的,多半是具有娛樂、消費性格的文藝商品。文學上的無出路,文藝青年的寫作量減少,或是寫出來也沒多少機會被人們讀到,或甚至更糟-即便讀到也挑不起什麼感覺。這應該足以解釋為什麼網路流傳的「文青一百問」裡,人們對文藝青年的印象只有種種消費品味,卻幾乎不提他們的生產行為。
是否,經過四十多年的黨化教育,台灣文藝青年已失去體查現實的敏感和切中現實的尖銳,一味向消費文化與自已的肚臍眼靠攏而淪為眾人嘲笑的對象?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文藝青年」令人又愛又恨,代表「文藝青年」四個字背後的精神或許並未隨著時代而消失,也就是「想要改變」。世人期待「改變」。張鐵志發表於2004年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成為暢銷書即為一例。台北唯一的基進文藝週刊《破週報》創刊十五年,遭受多方叫罵卻屹立不搖,也是一例。又如前面提到那個曾叫「文藝青年」樂團,部份團員後來加入「黑手那卡西」,以音樂詩歌全心投入社會運動。文藝青年血液裡「改變世界」的基因依然代代相傳,即便有些稀薄。
曾在文藝咖啡廳「挪威森林」擔任店員的黃士勛2009 年以Finn為名發表的歌曲〈文藝青年〉,其中唱道:
「我是/自以為的文藝青年/唾棄流行文化/大概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世界/我是/自以為的文藝青年/理想在哪邊/我想有人等著我/改變這世界」
雖然這種狂妄引來的訕笑從沒有停過,但現在台灣的文藝青年,也許正在摸索新的路,嚐試新的語言。只要「改變世界」的精神還在,難說不會再發生一次文藝復興運動。
這篇文章很有趣!!!!!!很好看的文青文,從歷史背景談及文青的前世今生過去未來。有意思!
“人們對文藝青年的印象只有種種消費品味,卻幾乎不提他們的生產行為。”
我很同意羅大哥上述這句話,所以當文青不知何時(也許在我出生前)逐漸成為貶抑,或是作為一種品牌或是品味;我還是比較願意甚至是有點天真的以為文藝青年就是(就只是)對文學藝術有興趣的青年,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就是文藝青年,畢竟我閱讀文學書籍也會對藝術有些興趣。
黎明翰,
謝謝你的肯定 ^^
我一直認為「文藝青年」應該要用文化生產力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單作為形象標籤是無意義的。
請問可以轉這篇到plurk facebook上嗎? 我會標明出處的 感恩
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