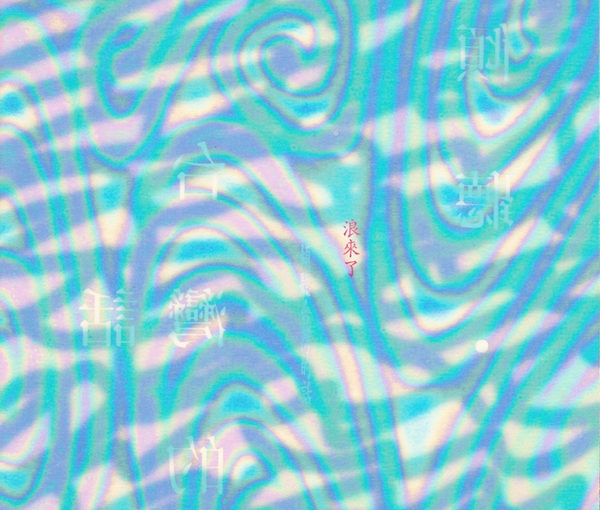* 本文發表於杭州美院學報《新美术》2016年 第6期 | 羅悅全
儘管田野錄音在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聲音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sound)、聲音生態學(acoustic ecology)的語境下有其方法論上的意義,但在2014年的展覽「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1]的部份主題展區裡,則嘗試離開這些已定義的學術框架,藉由史料的發掘與再脈絡化去發現田野錄音在台灣近代史中作為一種從解殖民、自我重新建構到走向作為一種藝術實踐與行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強調的是,對「造音翻土」來說,田野錄音的意義不僅是字面上的「於發聲現場收音」,而是「發聲-聆聽-紀錄-檔案化-再發聲(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再聆聽」的一連串過程。而台灣戰後田野錄音的採集意識如何辯證地發展,則是展覽所欲討論的重點之一。
在展覽開頭迎接觀眾的聲音,是台灣第一張完全自然音的田野錄音CD──《浪來了》,錄製於台灣東海岸,幾乎無人造音,僅有波起浪平一陣又一陣的海濤聲,長達47分鐘[2]。這段聲音是1994年夏天早上,參與一項原住民音樂採集計畫的錄音師符昆明在錄製花蓮阿美族部落的豐年祭之後獨自前往海岸,福至心靈錄下了這段自然之聲。水晶唱片於1997年發行這張唱片,在夾頁以一段冗長的文案說服聽者接受這張顯然無市場可言的錄音作品,其中提到:
早晨十時許,陽光、稻香、酒。之後,起床不久的錄音師離隊了,眼前海洋裡卵石的滾動,竟然如此清晰,於是他擺下了麥克風。左邊的麥克風靠海,右邊的麥克風近岸,浪從左邊來,石頭從右邊滾下,然後氣泡在中間呼吸。[…]在起興走向海岸的那一刻,錄音師究竟聽見了什麼聲音?是外界的浪濤?還是內在的心韻?對這個島嶼而言,阿美族之歌已經夠古老了,但是轉身而去的錄音師,顯然發現一些更原始的節奏。
細細解讀這張專輯,我們可以拆解出幾項意義,它一方面承接了台灣1960與1970年代間的「民歌採集運動」,以錄音去尋找「我們自己的聲音」的採集意識;另一方面,它也意味著田野錄音的採集意識的兩種轉向:一是錄音目標從樂音轉向非樂音;二是揭露錄音者在錄音紀錄中的主觀位置,更仔細地說,在學術性的田野錄音的方法學裡,錄音是客觀的,持麥克風的錄音者像是透明人,不存在主觀,但這張唱片卻期待轉遞錄音者自身的聆聽經驗──除了他聽到的海浪聲,還有他面對海洋時的心靈狀態與時空脈絡。這樣的企圖,就如同音樂哲學家彼得‧桑迪[Peter Szendy]用兩個提問所點出的一種當代的田野錄音觀念:「我們能讓一次聆聽被聽到嗎?我能否將我的聆聽傳遞出去,而不丟失其獨特性?」[3]
而《浪來了》這張錄音專輯所承接的「尋找自己的聲音」的採集意識,則必須從台灣日殖時代的田野工作說起。台灣最早的大規模田野採集是日本音樂人類學者黑澤隆朝在台灣總督府的支持下於1943年來台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環島錄音,其中包括原住民的歌唱以及漢人的戲曲,這批錄音為日後的民族音樂學者留下大量珍貴的研究資料[4]。然而必需要指出的是,這項採集計畫背後是意欲建立殖民地治理知識的帝國意識[5]。採集的目的影響了訪查過程,甚至也影響了錄音結果──受訪對象由日本警察或地方官員挑選出,部落歌者沒有拒絕的權力,幾乎是被迫接受錄音,並且在不願意唱部落禁忌歌曲的狀況下,刻意即興更改歌詞內容[6]。
台灣第二次大規模的田野錄音計劃發起於1960年代,許常惠與史惟亮兩位赴歐留學歸台的音樂教授有感於台灣學院音樂教育的全盤西化,在「我們需要有自己音樂」的民族意識召喚下發起「民歌採集運動」,組織兩組民歌採集隊,走遍鄉間錄下台灣當時尚存的傳統民間歌謠與戲曲[7]。民歌採集運動與黑澤隆朝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所欲找尋的是「民族音樂」的根源,藉以重建對自身的認識,而非以異國他者的身份進行人類學式的調查,也就是展開一種接近「自我民俗誌」(auto-enthnography)的聲音探索。[8]
但是這項錄音計劃的採集意識也同樣影響了錄音的成果──凡是不受認可的「非民族音樂」,都被排除在採集範圍之外。曾參與採集的中研院研究員丘延亮(當時還是大學生)指出,他所錄得的內容若有包含受到日本、西洋流行音樂影響的歌曲都遭到刪除,如今尋之不可得[9]。
有趣的是,大約與民歌採集運動同時期,並無嚴謹田野錄音的學術知識的鈴鈴唱片經營者洪傳興也出版了數十張「山地流行歌曲」唱片,那是他開著小貨車,帶上錄音器材與樂手,走遍東海岸,隨機吆喝部落裡的原住民前來唱歌,連原住民教會歌曲、日語歌曲都來者不拒地收錄於唱片中[10]。雖然沒有學術與文化上的企圖,這系列主要在部落裡流通的唱片卻因為忠實保留了原住民日常生活與歷史樣貌而在最近幾年重新受到文化研究者與聆聽者注意,這多多少少是因為地方意識於1990年代興起並蘊釀至今的結果。這種從聲音去探索本土的文化思維,主要來自於1990年代初發起《來自台灣底層的聲音》和《台灣有聲資料庫》兩項田野錄音計畫的水晶唱片。這兩項計畫從當代俗民文化的關注角度出發,蒐羅了曾被民族音樂學者排斥的俚俗聲音,包括金光布袋戲、電子北管、原住民近代歌謠。水晶唱片的企劃者何穎怡在一場座談中點出了這兩項田野錄音計畫所標示的採集意識轉向:
就我有限的經驗來看,我認為遷徙的歷史經驗最具體反映在台灣原住民的近代音樂裡。多數民族音樂學者對當代原住民音樂的研究興趣甚低,一來,音樂性上不夠原汁原味;二來,學者人力有限,搶錄正宗傳統原住民歌謠都來不及。但其實,原住民的近代歌謠出版一直很蓬勃。以往,它的通路集中在部落附近的唱片行。如果我們仔細聆聽這些音樂,便能看到殖民與遷徙的脈絡。音樂性上,它們兼容並蓄了傳統古調、歐洲教會和聲系統、日本演歌與那卡西、伴隨山清運動進入部落的救國團民歌、西方搖滾,到了這幾年,DX7電子合成樂器更使得原本便極具節奏性的原住民歌謠趨向電子舞曲化。[11]
本文前述的《浪來了》專輯,也發生在《台灣有聲資料庫》的採集計畫過程中,儘管它所紀錄的非樂音是這項計畫的「岔題」,無論如何,《浪來了》還標示了台灣田野錄音的藝術性轉向:離開人類學式的樂音聆聽,走向音景的聆聽,以及從錄音者的位置聆聽。然而,這張專輯在唱片市場上的失敗,也證明了這類田野錄音做為等待被聆聽的作品,難以在商業領域找到生存空間[12]。那麼,它應該發生在何處?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聲音」逐漸在台灣當代藝術領域內成為被越來越受重視的一種藝術實踐[13],台灣主要田野錄音採集者的身分從民族音樂學者、唱片製作人,逐漸拓展到當代藝術家,其所採集內容則從人聲、樂音、自然音,擴大至機械噪音、都會環境音乃至於日常生活事件,他們的採集意識比起過去,更明確是做為藝術實踐──運用田野錄音去做藝術的再生產。例如在姚大鈞催生下,由劉佩雯、李岳凌、陳立威、謝仲其於2003年組成的「台北聲音小組」;2004年發表的「台灣聲景計畫」的蔡安智;於2010年啟動「台灣聲音地圖計畫」的吳燦政;由黃大旺、張又升與陳藝堂於2011年組成的臨時團體「民国百年」;於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發表〈咱的作工進行曲〉的王虹凱……。而在展覽「造音翻土」所邀請的參展藝術家:定居於台灣的法國聲音藝術家澎葉生[Yannick Dauby],以及黃孫權與複島團隊,他們的田野錄音,不僅是創作的方法,更可視為一種藉由聲音召喚地方認同與革新的社會行動[14]。
瑞士聲音藝術家兼作家莎樂美‧沃格林[Salomé Voegelin]曾如此描述她對田野錄音的期待:
或許我們應該一起停止錄音,只簡純地聆聽。但我相信,田野錄音的未來在於一種張力,這種張力來自於我們透過參與、合作、擴展與玩耍來變化我們聽到的聲音,透過這些,我們可以在其中嘗試一個共享空間的謙遜人性,並且與真實世界再協商。[15]
沃洛林認為田野錄音的未來應該在於透過聲音的紀錄、變化與聆聽,去對真實世界提出回應。她所說的「謙遜人性」指的是:「不尋求擁有這個世界的聲音,不是要去認知並吞食它,而是去理解我們就是這個音景的一部份」[16]。而黃孫權則更直接簡明地提出類似的看法:「田野的目的不是為了做作品,而是嘗試回答地方與空間提出的問題。」[17]他們的看法某程度上正適合用來說明台灣田野錄音七十多年來的辯證──殖民/反殖、他者/自我、固著的傳統/流動的變遷、樂音/非樂音、客觀/主觀、真實/形構──所朝向的方向。以田野錄音為主要創作方法的藝術家,在此期待下,除了是聆聽者、錄音者、蒐藏者、發聲者,更被賦予了新角色--謙遜的行動主義者。
[1] 「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何東洪、鄭慧華與羅悅全策展,展於台北北師美術館(2014)以及高雄市立美術館(2014)。
[2] 單就形式來說,放在世界的範疇,完全海浪聲的錄音出版品並非創舉,例如美國大西洋唱片[Altantic Records]於1969年發行的《Enviroments 1》。但《浪來了》的採集與發行的動機與這些西方的環境錄音唱片無直接關連。
[3] 來自以下文章的引句,Lawrence English, “A Beginner’s Guide To Field Recording”, Fact, Nov 18 2014。中譯出處 http://www.wtoutiao.com/p/1ffmpll.html ,顏峻譯。
[4] 在1943年之前來台進行田野錄音調查的日本學者還包括北里䦨、田邊尚雄,但規模不及黑澤隆朝。
[5] 范揚坤〈以台灣為名:民族音樂、田野錄音及其反思〉,《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立方文化與遠足文化聯合出版,2015。
[6] 周明傑〈一甲子的邀約:日本文獻當中僅存排灣族歌者的追蹤報導〉,《文化生活》,屏東縣立文化中心,2004年10月。
[7] 同註5。
[8] 同前註。
[9] 〈民歌採集運動與青年下鄉:丘延亮的回憶點滴〉,何東洪、羅悅全訪談,《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立方文化與遠足文化聯合出版,2015。
[10] 黃國超〈台灣戰後本土山地唱片的興起:鈴鈴唱片個案研究(1961-1979)〉,《台灣學誌》,2011年10月。
[11] 「座談會整理-從音樂遷徙談文化認同」,中山大學西子灣站,2001.9.1,
[12] 但是以自然田野錄音混合樂音的「自然音樂」在台灣唱片市場仍有成功的例子,如吳金黛於1999年起所發表的一系列「聽見大自然」系列唱片,這系列錄音作品採取了折衷主義的作法:在兩張一套的唱片中並陳自然音,以及混合了自然音的樂音。
[13] 自2003年於台北舉辦的「Bias異響國際聲音藝術展」之後,「聲音藝術」一詞開始在台灣藝術領域頻繁地出現。
[14] 參閱:澎葉生〈田野錄音與傳統音樂的再生〉、黃孫權〈複島計畫與歷史中的聲音:高雄點唱機裡的社會圖景〉,《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立方文化與遠足文化聯合出版,2015。
[15] Salomé Voegelin, “Collateral Damage: New field recordists put themselves in the sonic frame”, The Wire, Issue 364, June 2014.,中譯為本文作者。
[16] 同前註。
[17] 同註14。